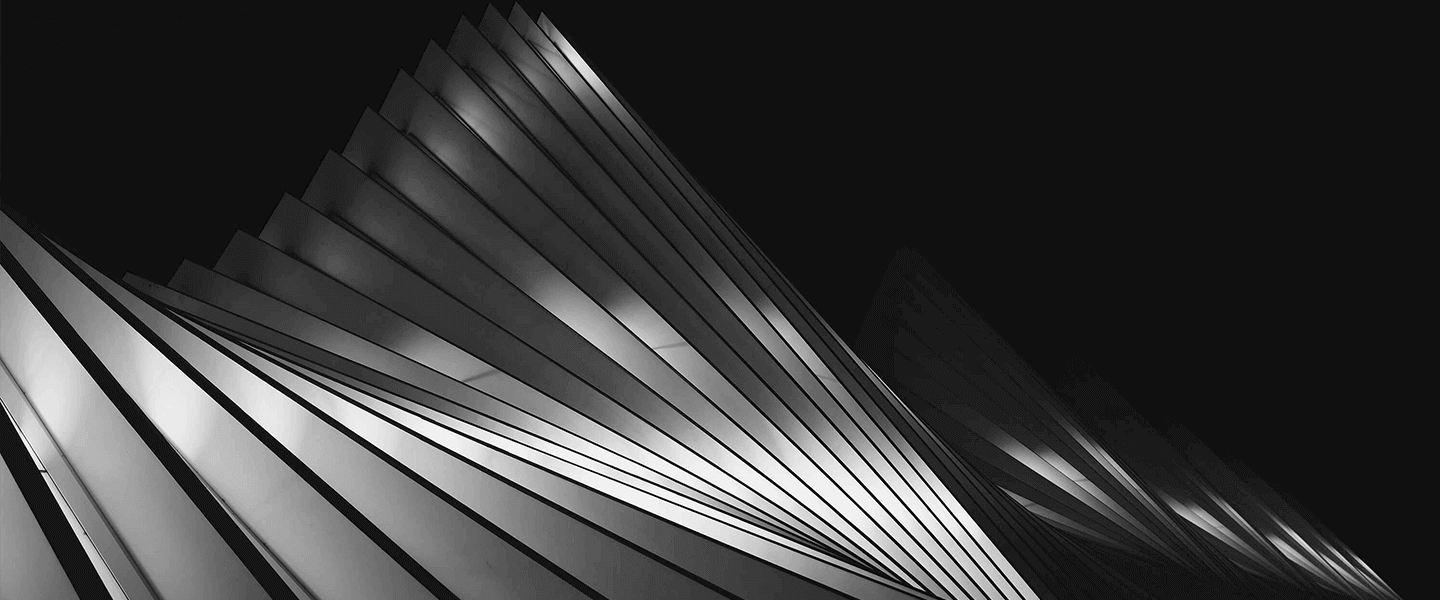『“乡情乡韵”』
· 碗底有字·
/ 第130期 /
———————
文: 陈松泉
01
过年的时候,无意中翻出一只用报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,一次也没用过的旧碗。孙子看到碗底刻有一个笔划粗的“泉”字,好奇地问我:“碗底怎么有个字啊?”面对此碗,勾起我许多沉睡的记忆。我对他说:“这‘泉’字,是我名字中的一个字。它是我亲手凿上去的。表示这碗是我们家的。”然后跟他说了为什么会在碗底刻字的因由。
02
碗底刻字,是以前农村中家家户户必须要做的事情。以前的农村,每家每户都不富裕。不仅碗底刻字,其他的家具和农具上都会刻上字,或者用油漆写上某某村某某人某年某月某日添置。村里人家婚丧嫁娶办红白喜事时,桌椅板凳、条箱提盒、碗筷酒杯等等都要向左邻右舍借。事办好后,邻居们按器物上的姓名一一归还。如果有碗摔碎了,办事的人家就会买个新的赔偿给他们。
每年过年前,家家户户必定会添置一些新碗碟。要添置多少新碗碟呢?一般就得先把家里的旧碗碟全都拿出来,把没有一点点磕破的挑出来。数一数。因为,祭祀时用的碗碟必须保证丝毫无损。少几只,就去卖碗碟的店里参考这个数字,逢五逢十地多买几只新的回家。店家知道买碗人都会要求在碗底刻字,所以他们要求买碗人必须亲笔写下需要刻的是哪个字。如果不会写字的人去买碗碟,一般都会带上预先写好字的纸去。刻字,是按字计费的。所以,碗碟上一般就刻一个邻居们可以识别的字。以前的人大都取双名,前一个字表辈分,后一个字区分兄弟。店家刻字,开始的时候,是用一根小钢钎,用锤子一笔一划地敲打,笃笃笃地凿出字来,后来有了专门刻字的电钻,他们熟练地使用电钻,好像我们常人写字一样,一会儿功夫就刻好了。刻一个字,具体几分钱,我已经不记得了。
03
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和妻子步行去新市逛店。中饭后,走进一家碗店,看到青花宝相花纹的碗,我俩都感觉清丽雅致,原打算买一桌碗(12只),后来为了预防以后不小心打碎一只也能凑齐一桌,就买了16只。由于碗店生意很好,等待刻字的人也多。我自以为用个小钢锥自己也能刻。于是,拿上碗,就到西河口去寻找我们西庙桥村来新市的船。西庙桥每天有好多划着小船或者摇着大船到新市街上买卖东西的人。走着去的人,买了货,不方便随身带回去的,一般都会去西河口寻便船,请他们帮忙带回去。然后,回家,到他家里去拿就是了。有时我们也会乘便船回去。乘船,可不能白坐船!扳桨、把艄,撑篙、摇橹的活儿,我们也会主动争着去做。出力,才心安。“我为人人,人人为我。”这是我们村里人淳朴报恩的自觉行为。
新碗到家后,我就迫不及待地借了一根细小的钢锥,拿个小槌,小心翼翼地叮叮叮地在碗底凿字。当“泉”字凿成后,兴奋地展示给家人鉴赏。奶奶看到“泉”字,似乎大难临头一般,不悦之情溢满着整张脸。我疑惑地压低声音问:“刻得不好吗?”奶奶说:“你这个人啊,这么大了,还这么不懂事啊!现在这个家是你爸爸在当家!你怎么可以在碗上刻上你的名字啊!”遭此棒喝,我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非常出格的事。那时我虽然已经有了自己的儿子了,但按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,我真的还没有资格在碗底上刻自己的名字。这“泉”字碗,就在那天被我用报纸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,藏在五斗橱的一个角落里。
04
现在,农民的钱包鼓起来了。红白喜事,自有一条龙服务,再也不用向左邻右舍借东西了。东家开开口,包装好的出租消毒餐具等都会送上门。买新碗,再也不用刻字了。
图片来自网络
执行主编:归李喆